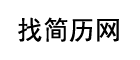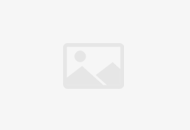十字绣中的全针绣是什么意思
十字绣的基本绣法之一,搜索就有答案了,给你复制一篇。
1. 全针绣法(X)
先由网眼1穿上来,再由网眼2穿下去,再由网眼3穿上来,再由网眼4穿下去,再网眼5穿上来,再由网眼2下去,再由网眼3上来,再由网眼6下去,以次类推。
2. 半针绣法(1/2X)
半针绣是一条对角线构成的,即为全针绣的一半。
3. 四分之一绣法
1/4针绣是由对角线的一半构成的,如果要边线正方形中残留的部分,表现不同颜色,则需要有1/4针绣来表现。
4. 四分之三绣法(1/2X)
3/4绣是由一条完整的对角线与半条对角线所构成出“人”字形状。
5. 回针绣法(边线)
第一针由网眼1上来,再由网眼2下去;第二针则由网眼3上来,再由网眼2下去,再由网眼4上来回到网眼3,除了第一针,其余每一针都是以回针的方式回到原穿上来的网眼中。回针一般用于绣过线、轮廓和字母。
6. 法兰西结
把针举到1的位置穿出,将线绕针一圈,把针插在2的位置。用不绣花的指握住绣花线的端部,把结拉紧,而后将针穿过织物,把住绣线,直到必须松开为止。若打大结,可适当增加线的股数,但只缠一次。
黄金满地十字绣 长2米宽一米 我妈绣了一年了 请问大约能卖多少钱啊准确点谢谢/。。。
十字绣成品价格计算公式(专业级):总绣格数*0.025元/格*1.015的(总绣色数-1)次方举例:单色价格:总绣格数*0.025元/格*1双色价格:总绣格数*0.025元/格*1.015三色价格:总绣格数*0.025元/格*1.015的2次方以此类推说明:0.025元/格是按50元/天的人工费计算的(实打实8小时计,扣掉了吃饭喝茶上厕所的时间了),你可以按照当地的人工费标准作出调整.如果你觉得你的人工是20元/天那当然也可以,就只要把0.025除于50再乘于20就行了.绣过十字绣的人都知道,颜色的多少和绣工时间是成倍增加的,有的地方一种颜色只要绣一针,同样需要挑线、换线、穿针、起针、收针,5分钟绣出一针还算快的哪。如果看花眼绣错格的话麻烦就更大了(颜色多了这种事经常会有)。总绣格数是实际绣格数,可不能把空白格也算在里面,有失公道,但总不见得一针一针数啊,教你一方法,点好总行列数,两者相乘,算出总格数,再看一下绣的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八九不离十),将总格数乘于该比例就行了,另外,买套件及裱框的成本要加上去啊。我没见到你妈妈绣的成平,根据长2米宽1米的尺寸,大概估价在6000-8000左右,而且还要看绣工如何,绣工好的话可以把价格调整为7500-8500左右。
十字绣里面的,是什么字?
您好亲,十字绣里面的,字是家和万兴。【摘要】十字绣里面的,是什么字?【提问】【提问】【提问】您好亲,十字绣里面的,字是家和万兴。【回答】您好亲,针对您刚刚提出的问题,为您提供以下内容:十字绣(cross stitch),是用专用的绣线和十字格布,利用经纬交织的搭十字的方法,对照专用的坐标图案进行刺绣,任何人都可以绣出同样效果的一种刺绣方法。十字绣是一种古老的民族刺绣,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许多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一直以来就普遍存在着自制的十字绣的工艺品。由于各国文化的不尽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字绣在各国的发展也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无论是绣线、面料的颜色还是材质、图案,都别具匠心。挑花是一种中国古老的传统刺绣工艺,它分布广泛,其中湖北黄梅挑花发源最早、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在中国挑花工艺发展史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黄梅挑花”也是各挑花的代表和统称。2019年12月,河北发布42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名录,其中包括十字绣。【回答】
十字绣迎客松万里长城代表什么含义?
迎客松万里长城画面优美、立体饱满:靑松迎客挺立起点,长城万里似巨龙盘旋,漫山遍野青松苍翠,双流瀑布源源不断,一轮红日初升云海,漫山雾霭似轻烟弥漫。整幅画因青松翠柏而生机盎然,因飞流急瀑而鲜活灵动,因云海薄雾而飘逸出尘,因红日初升而充满温暖和希望,令人一见即生舒适安逸之感
迎客松万里长城在提升家居品味、活跃整体氛围的同时,还具有很多的文化内涵和风水寓意。万里长城象征前程似锦、鹏程万里,飞流瀑布寓意财源滚滚、生生不息,红日初升似鸿运当头,双石护卫寓双石开泰。整幅画藏风聚气,寓意吉祥
有关晋朝的民风民俗,如服饰,佩戴,礼仪习俗,节日,家庭关系,吃住行等。写小说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融合的范围极广,几乎包括了中国长江、黄河、辽河、漠北广大区域。北方各民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卢水胡各族先后建立政权,将社会组织模式乃至文化习惯带到中原;南方的山越、蛮族、茎人、俚人、僚人也走出深山老林,开始与汉族融合。
南北朝裤褶1
民族大融合带来了南北社会组织形态的激烈变动。北方割据政权大体都经过“胡汉分治”的阶段。所谓胡汉分治,就是对于境内少数民族采用本族制,而对于境内汉族则采用汉制。直到北魏太和(477—499年)初年,才逐渐用汉族的原有办法改革地方基层管理。太和九年到十年 (485—486年),均田制、三长制、州郡制相继出台。三长制规定每五户百姓置邻长,合五邻置一里长,合五里置一党长。太和十年,北魏下令在全国设置38个州,同时对畿内地区居民实行分并改组。北方地区重新纳入秦汉以来的州、郡、县的组织结构。魏晋南朝的汉族政权虽然社会组织方式与秦汉基本相似,沿用州、郡、县的管理模式,但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势力大为膨胀,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门阀士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士族也迅速发展。南、北士族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建有田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个体小农虽然也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往往沦为士族的奴婢、豪强的佃客。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六大著名稻作区。它们是江南稻作区,包括三吴、皖南及晋陵地区,它是南朝最重要的稻作区;荆湘南川稻作区;汉中巴蜀稻作区;南阳盆地稻作区;淮南稻作区;交广和闽广稻作区。这些稻作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农业在全国经济中的低下地位。南方城市的密集度也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其中尤以扬州、荆州、益州 、广州四个地区城市最为密集。
南北朝裤褶之2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食为稻米、小麦。在面食制作方面出现了很多变化,西晋束皙的《饼赋 》提到新出的面食有安乾、豕耳、狗舌、剑带、案盛、髓烛等名目。它们有的由普通百姓发明,有的从外族传入中原。这一时期,中国菜肴的九大主味:酸、甜、苦、辣、咸、鲜、香、麻、淡等都已具备。汉代已知如何用曲酿醋。北魏时,用谷物制曲酿醋的技术相当成熟。《齐民要术》中有多种制曲酿醋法,而且还开创了酿造陈醋的方法 。先秦时只有肉酱“醢”,汉人已用豆作酱。《齐民要术》有《作酱法》,专章介绍13种风味不同的酱的做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不少菜肴的做法来自外域。本是胡人喜食的乳酪,成为北方汉人广泛流行的副食。还有一种菜肴,叫“羌煮貊炙”。据《齐民要术》介绍,羌煮原是羌人的一道菜,吃法是将精选的鹿肉煮熟后切成块,蘸着各种调料制成的浓汁吃;貊炙是貊人发明的一种烤乳猪,做法是用火慢烤,一边烤,一边往上洒酒抹油,烤熟的乳猪色泽鲜丽, 呈琥珀色,入口即化,汁多肉润,是上等美味。
魏晋南北朝时期,讲究服饰之美。体衣(上下衣)、头衣(冠帽)、足衣(鞋袜)成为人们典型的装饰式样。当时服饰更新速度很快。《抱朴子·饥惑》曾说,当时冠履衣服,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化,“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经常突破等级限制 。胡服在当时十分流行。十六国、北朝时,胡服在黄河流域达到与汉服平分秋色的程度。直到孝文帝改革后,服饰的胡化风气才有所改变。
魏晋南北朝的婚尚以等级性婚姻为典型特征。世族享有特权,他们把血统、门第、出身当作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及身份价值的尺度,婚姻也竭力保持血统的纯化,因而形成了世族婚姻的两个特点:一是重门第。南方世族之间依据政治地位、社会名望和家庭势力构成了比较稳定的婚姻圈。琅笽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三者之间的通婚最繁,其他如河南褚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等虽与王、谢通婚,但政治地位、家族势力有所不及,频率不高。与北方大族崔氏、卢氏联姻的,绝大部分都是有一定郡望的世族。可见当时南北方的大族 ,对于婚姻等级界线划分得十分严明。二是地缘性因素比较突出。如吴姓大族中以吴郡顾 、陆、张氏同会稽孔氏和吴兴沈氏五者通婚最密,而以吴郡顾氏、陆氏、张氏三者婚嫁较繁 。等级性婚姻造成早婚现象非常普遍。如东吴郁林太守陆绩之女,年方13就嫁给同郡张自,东晋荀羡年15岁就与帝室联姻。梁武帝纳丁贵嫔时年14岁。陈朝周弘正年10岁时,河东裴子野就以女妻之。早婚自然早育,这就造成了兄弟姊妹年龄悬殊、而叔侄姑侄之间年龄反而相近的现象,遂使高频率的血缘异辈婚姻成了这时门阀婚媾的一个显著特色。
南北等级性婚姻习俗虽然大体相似,但也略有不同。在继娶纳妾方面,南方的正室侧室之分及嫡庶之别,不如北方严格,家庭纠纷亦不如北方严重。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南北也有不同。北方受少数民族胡化的影响,妇女与社会接触较多,地位较高。家庭的组织形式和家庭情感 ,也复有南北之别。南方形成了父子异居和一门数灶之风。
魏晋妇女发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特别重视葬事,但对葬礼却并不十分重视,而重视至情至性的哀悼。西晋王戎在母丧期间,饮酒食肉,不拘礼制,但内心十分悲伤,容貌憔悴。东晋会稽王献之死,其兄王徽之奔丧不哭,因为王献之喜好弹琴,王徽之将王献之的琴取下来,坐在灵床上试着弹一曲 ,但怎么也弹不出和谐的音调,他把琴摔在地上,悲痛地感叹“人琴俱亡”,恸绝良久(《 世说新语》卷下《伤逝》)。当时比较重视相墓术。郭璞、张子恭、高灵文等是当时的相墓大师。相墓术除了继承天人感应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外,还十分重视审察山川形势,讲究墓穴的方位,向背、排列结构等,其中山川形势的勘察最受注重,它涉及山脉、水流、林木的位置、走向、枯荣,看重山川的“形”、“势”、“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宗教信仰较为强烈。佛教和道教都拥有大量信徒。秦汉时期所确立的祭祀天地之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个别皇帝举行以外,并未得到高度重视。而对佛 教和道教神佛的崇拜却与日俱增。道教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神仙谱系,它虽然没有超越固有的 宇宙观念,仍以天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岳镇、海渎、山川作为构造神系的主干, 但在道教神系中,神的形象更加富有感染力,不像国家祭典中那些偶像那样严肃,较少政治 色彩。而且道教还认为有“真人”、“仙人”,他们是得道而有神通的活生生的人,这些人又多是传说中的人物,如赤松子、彭祖、王乔之类。南北朝期间,庐山曾建有招真馆,衡山建有九真馆,桐柏山建有金庭馆,茅山建有曲林馆,对道教神仙进行祭祀。寇谦之、陆修静对祭祀道教诸神的祭礼还有所规范。佛教的神佛体系主要包括佛、菩萨、天王(护法神)、力士。佛教神佛谱系既不像儒家国典化的神系,也不像道教神系。对佛教偶像的崇拜主要包括佛诞节、成道节的纪念仪式、寺院日常礼拜仪式。举行上述仪式, 以香花供养为主,反对杀生。
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神祀也日益庞杂。精怪迷信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木、石、兽、禽都被认为可以成精作怪。在各种精怪之中,当时人们对龟精、獭精、鱼精、山精、狐精、鼠精尤为迷信。这些精怪或为妙龄少女,或为英俊少男,或为皓首宿儒,变化多端,体现出人们受宗教观念影响后对于大自然的艺术改造。
浮生六记与中国民俗的关系
一篇文章中,针对《妇女杂志》进行的一次“配偶选择”问题的问卷调查,批评这一调查结果所显示的青年太重“男女相互的受慕”,不重视关乎生育后代的“身体健全”因素,男子不重女子“能操家政及教养子女”的能力,甚至有“不得理想之配偶则无宁独身”的倾向及迟婚倾向等,批评这些择偶观是“浪漫成分太大”、“个人主义之色彩太浓”,认为是丢掉了传统而盲目学习欧美的恶果:“国人学步欧美,不图竟合节奏若此也”[115]。
潘光旦在“种族竞存”家庭观念的观照下,《浮生六记》沈复夫妇作为个人主义婚姻观的一个象征符号,自然受到否定性的评价,故被他判定为不应当作为“恋爱生活的规范”。
第二,潘光旦对于青年喜读《浮生六记》现象所反映出的混淆理想与现实的恋爱至上主义,对于婚姻缺乏科学态度的倾向予以批评。
由潘氏的注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近代青年”“很喜欢阅读……沈复《浮生六记》一类的书”,以及青年们把这一类书“当恋爱生活的规范与金科玉律看”这种现象,明确指出“那是一大错误”。他主张对于婚姻家庭应当以科学的、现实的态度来对待,而不应当以脱离实际的幻想作为指导现实生活的准则。
“恋爱至上”是“五四”以后青年中盛行的新婚姻观,潘光旦则由社会生物学者的立场,撰写多篇文章反省这一社会思潮,批评这种婚姻观是不科学、不理性、不现实的。他批评青年们热衷于恋爱至上婚姻生活的浪漫幻想, “青年人所称道不衰的恋爱,大都是耳鬓厮磨式的所谓浪漫的恋爱,他们以为这种恋爱可以维持永久,真正圆满的婚姻生活应当始终以这种恋爱做衬托。”[116]但现实生活却并非如此,结果往往造成青年的失望和婚姻悲剧,他说: “一个人,决没有一生都是在恋爱中过活的。最近,常见一般青年,初恋的时候,是很热烈的,等到结婚以后,恋爱的兴趣渐低,甚至于消失,于是就认为是感情破裂,双方非离婚不可,这是极端错误的。”[117]他以生理学和心理学为依据,宣传科学的性爱理论,指出:“性爱是一个生物的、心理的、与社会的现象。”[118]两人的恋爱不可能割裂开社会关系和实际生活而孤立永恒地保持。恋爱至上主义是把脱离实际的虚幻理想当作了现实的准则,这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以这种观念作用于社会,则会造成种种危害:“适用于思想,则成种种玄学观念。若适用于社会改革,则其产果即为各色之乌托邦或各种臆断之主义。”[119]所以,他反对青年们热衷于充满恋爱浪漫情调的《浮生六记》一类书,反对将沈复夫妇的浪漫婚姻作为现实生活的楷模,认为这是一种不现实、非科学的婚姻态度。
第三,潘光旦批评“一部分文人的提倡”, 造成青年热读《浮生六记》一类书并崇尚个人主义婚姻观,这些文人是以非科学态度误导青年。
潘光旦所主张的种族竞存的优生观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人类的进化竞存不完全是自然命定完全被动的,人不应盲从于生物进化律,而是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人可以用理智和经验来作出适于优生进化的选择,从而建立符合优生原则的婚姻家庭制度。而承担这种建构新制度新观念责任的,首先应当是掌握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负有社会责任,特别是负有教育青年责任的文化人。但“一部分文人”向青年提倡《浮生六记》所代表的个人主义婚姻观,这是违背科学精神,也是对社会和青年不负责任的。在他看来,如果说青年还未经过家庭生活的实践,不了解婚姻家庭的真实情况,因而抱有恋爱至上的幻想还有可谅解的一面,那么,作为经过了家庭生活实践、了解婚姻真实情况,又负有教育和指导青年责任的教育者、文化人,却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婚姻家庭问题,而将不切实际的幻想作为指导青年实际生活的准则来提倡,这则是尤为错误的。
他在1930年对几位教育名人的婚姻家庭观所作的评论中,就曾集中讨论了这一问题。他的这篇评论起因于《申报》的一篇新闻报道,文中报道了国民政府立法院宴请“全国教育会”全体会员,席间主会者向这些教育精英询问当时青年中热烈讨论的对于姓、婚姻和家庭存废问题的意见。报道中记述了蔡元培、蒋梦麟、吴稚晖、李石曾、张默君、钟荣光等八人的回答意见,他们都是当时教育界最有名望和影响力的权威人物。但这八位人士的回答,除了敷衍说笑话及模棱两可之外,有明确意见者可归为两条:一是主张或赞同废除婚姻和家庭,钟荣光和蔡元培即主此说;二是认为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马上废除,但不远的将来必然废除,如蒋梦麟说五十年后必然废除,李石曾说由存向废是必然趋势。潘光旦对于这些教育权威人士的态度和观点十分不满,遂写了一篇评论,对他们的发言提出尖锐批评,并指出“这个批评,并且可以适用于其他切心于社会改革的人。”[120]他批评这些教育家对于婚姻家庭问题缺乏科学的认识态度。指出这几位教育界权威人士, “在青年视听集中于少数权威身上的今日的中国”,在立法院举行的正式宴会上回答正式询问的公开发言中,却极为缺乏教育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及讨论问题的科学态度,他们回答的“这许多话中间……几乎没有一句像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口吻。”[121]他认为,从人类社会的有机进化观和人类经验来看,婚姻家庭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还未看到必然要归于消灭的迹象:“理论上,从种族、社会、与文化的需要方面看去,或实际上,从西洋各国已经得到的经验看去,似乎是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制度,它们的枝节纵可以增损,而基础的结构是不可少的。”[122]因而他针对蔡元培主张废除婚姻和家庭,并设计了一个没有婚姻和家庭的理想村的发言,指出蔡氏“论婚姻的理想,真是美满极了,无奈行不通何,无奈与社会的联络性绵续性太相刺谬何?”[123] 他批评蔡氏“自己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组的组长,谅来决无不了解这一点初步的社会学智识之理”[124]。潘光旦对这些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教育界权威人士,以这种非科学的态度提倡废除婚姻家庭,以不负责任的轻率态度向公众谈论这一重要的现实社会问题,表示了极大的愤懑,认为这是误导青年、贻害社会。
由上可见,无论是他批评热读《浮生六记》一类书的青年,还是批评提倡这类书而误导青年的“一部分文人”(其中应当也包括俞、林二位这样的提倡者),他指出的一个共同病症就是这些人对于婚姻家庭问题,都缺乏科学的态度和立足现实的认识方法,因此才会产生错误的婚姻家庭观。他认为,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来建构有利于种族竞存的新家庭观念和制度。那么,这种科学方法是什么呢?他认为:“以言观点,则为生物演化的;以言目的,则种族价值之提高居大半;以言方法,则重事实而轻浮词臆说;以言实际之兴革,则认旧制度有相当之价值,而宜利而用之。”[125] 以生物演化为理论,以种族图强为目的,以尊重事实为方法,以现有制度为基础——这就是他所主张的认识婚姻家庭问题的“科学方法”。
那么,由这种“科学方法”,他得出了怎样的婚姻家庭观念呢?他认为,西方由个与群的对峙观念,形成了个人主义“小家庭论”与社会主义“无家庭论”这两个极端形式[126],都是偏颇的,都不利于种族竞存。他认为,基于中国现实应取兼顾个群的家庭观,采取折中家庭形式,即包括老、壮、幼三辈的单系主干家庭,其他成年子女分居但也赡养父母。他认为这是社会学家“瞻前则有演化事实为之张本,顾后则抱有循序渐进之志愿”,“不为理想和成见所蒙蔽”而作出的判断。[127]实则这也是当时一般中下之家比较普遍的家庭形式。他认为,折中家庭制度有两大益处:既有利于“种族精神上与血统上之绵延”而具有“生物效用”,又有利于“训练同情心与责任心”而具有“社会效用”。与中国旧家庭制度相比,则“去旧日家庭形式,而无害于其承上起下之推爱精神”。[128]可见,在家庭关系上,他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种族绵延”和“同情心与责任心”等群体利益的一面,而不是个人幸福的一面。
潘光旦对于《浮生六记》现象的解读,通过上述对其内含的三重涵义进行的分析可知,其中的思考涉及到建构家庭观念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问题,从这一点来说,潘光旦比俞、林二氏的解读具更为深刻的意义。他特别提出了作为负有社会责任的文化人,应当以什么宗旨和态度来对待传统,来研究社会问题,并以何种方式传达于社会。他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文化人及一般青年对于婚姻家庭问题缺乏科学态度的弊病,倡导以科学态度认识家庭问题,用科学方法来建立新的家庭制度和观念。
由今天的眼光看,潘光旦所提出的折中家庭形式,基本适合于当时及此后至今的中国广大农村及部分城镇,即社会福利还不能解决养老与抚幼问题的前现代及不完全现代社会。但潘氏的优生学家庭观,也有过于强调种族竞存的群体利益,强调以后代优生为中心,却对个人幸福及利益有所忽视的偏颇,而个人的幸福及利益,毕竟是工业化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方向。家庭作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基本组织,其观念与制度形态,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个人与群体利益协调的结果。就家庭而言,个人幸福与社会和谐、种族繁衍这三者之间,究竟怎样协调,应当是个依不同社会条件而不断调整的过程。
结语:三种解读理路之比较
由上可见,《浮生六记》这个传统时代几被湮没的民间小家庭生活的平凡故事,到了“五四”以后,却由于价值系统和话语体系的改换而被重新唤发出了新生命力,俞平伯、林语堂和潘光旦就是以新的眼光重新解读此书的三位代表人物,而且由于他们各自价值系统和话语体系的差异,而赋予了该书不同的符号意义。俞平伯是从一位新文学青年的立场,由启蒙主义的认识理路而将之作为“个性解放”的符号,纳入到个性解放-民族自强的启蒙主义话语体系而赋予了正面的意义。林语堂则是从一个介于中西之间的边缘文化人立场,由西方视角将之作为“闲适生活”的符号,纳入到后工业主义及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从另一个角度也赋予了正面的意义。而潘光旦则从一位社会学家的立场,由优生学的科学方法,将其作为“个人主义婚姻观”的符号,纳入到种族竞存的家庭观念体系中而赋予了否定性的意义。他们三位分别代表了“五四”以后二三十年代新文化人中相当流行的启蒙主义、西方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三种认识取径,而他们对《浮生六记》一书所作的不同解读,则反映了此书所代表的一种民间传统,在这三种现代家庭观念建构理路中所具有的不同意义,其中蕴含着传统在现代观念中延续与变异的一些特点,下面作一比较分析。
首先,他们三位的解读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以新的文化视域对《浮生六记》作了一种话语的转换,从而使传统元素转变为某种新观念的符号。
他们三位都生于世纪之交,成长于“五四”时期,受新式教育,也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新文化运动,都有新文化思潮的背景和思想影响,属于新一代文化人,形成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价值系统和话语体系。与他们的前几代文化人相比,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话语转换”。从价值系统方面他们都已经抛弃了传统儒家观念而代之以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如俞、林二氏推崇个性观念,潘氏的科学观念,都是与现代民主、科学精神一致的。从话语体系方面他们都自觉地接续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理念及其表述,无论是启蒙主义、西方视角和科学方法,都属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而与中国传统知识谱系已截然不同。从认知立场方面他们也都脱离了文化“卫道”的传统定位而抱有深切的民族振兴关怀,这也是“五四”一代文化人的共同情结。他们就是在这种共通的新文化视域下对《浮生六记》重新解读,而《浮生六记》的面貌和意义也正因这种“话语的转换”而幡然改观,由旧视域下几无意义的琐屑卑文,一变而为颇有价值的新观念符号。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话语的转换”,使此书文本的本来意义,在他们的解读中发生了某种误读和扭曲。细察他们的认知思路,都是在新的文化视域下,将该书文本的原来意义体系肢解,从中抽离出某种元素,赋予了新观念的符号意义——个性解放、闲适生活或个人主义婚姻观。这种符号意义虽与文本中的原体有某种重合或貌似,但由于这种元素已经被抽离开原来文本的意义体系,并被附加了一些新的意义,因而在性质上也已发生了某种改变,经过这种“变质”后而与新观念符号对接,再被置入他们各自新观念体系之中。但此时的传统已非原来的传统,却也正因其原来的生命部分地死亡,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是传统在现代观念中延续的一种悖论式命运。一种传统就这样经过元素抽离——话语转换——变质——成为某种新观念符号——最后被纳入到新观念体系之中。——这就是他们三位对《浮生六记》的解读,给我们构画的一种传统元素如何在现代观念中复活并延续的线路图。也就是说,传统是以某种“变异”了的形态存在于现代观念之中。应当说,在现代观念建构中,这样一种传统延续的方式是颇为常见的,直至今日的文化建构中也多有沿袭,只是沿用这种方式的人往往对此甚少省察,故常将“变质”后的传统误认为原本的传统,从而造成某种认识的歧路而不自知,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轻率结论,引起无谓的纷争。因而重要的是,这种使传统因素“变异”的机制为何,俞、林、潘三位恰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用来比较省察的例子。
第二,他们都将《浮生六记》所代表的民间传统作为建构新观念的内在资源,从而使现代家庭观念接续上了民族传统之根。
他们三人作为“五四”一代新文化人,其建构新观念的基本知识主要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知识,而对于传统文化,依我们以往的通见,他们也自然具有与“五四”一致的决然“反传统”倾向。然而由他们对《浮生六记》的解读可知,他们却非一概地反传统,或非反对一切的传统。至少《浮生六记》所代表的一种传统在他们的新观念建构中,显然就不属于一概被“反”的行列,反而是一种内在的文化资源(潘氏之“反”,亦是“反”中有“护”的成分)。实则在他们的传统文化储备中,固然有正统儒学一类已被列于“反对”行列的一脉,但同时还有《浮生六记》一类以往属于异端、居于下位的民间传统一脉,而正是这后一脉是他们所亲近、所包容,甚至加以借助和赞赏的,并且成为他们建构新观念的一种知识资源。
他们与《浮生六记》的相遇并非偶然,由他们留下的大量文字可以看到,他们都对民间传统文化抱有浓厚兴趣,都阅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最早推介《浮生六记》的俞平伯,后来以毕生精力专研世俗小说《红楼梦》,显然民间文化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系;洋派文人林语堂由孟姜女故事的“启蒙”,以及专举民间文化推许为中国文化的精华,所述文字中常引野史小说,亦足见其对民间文化的偏爱;而坚守科学立场的潘光旦,虽然批评青年热读《浮生六记》一类书,但由他以明清野史作为开始心理学研究的资料,到《性心理学》译注中征引旧时笔记小说竟达百余种之多[129],可见其对民间文化的熟悉与积累。这些都表明,他们三人对民间俗文化都有着共同的爱好,且是他们建构新观念的重要知识资源。正是这种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利用,使他们将现代观念在传统中找到并接续上了民族文化之根。环顾“五四”后直至三四十年代的文化界,流行着一股“民间文化热”,许多著名文人将民间文化作为治学的材料,诸如新学领袖胡适作《〈醒世姻缘传〉考证》、国学大家陈寅恪作《柳如是别传》,乃至对《红楼梦》阐释与考证的风行竟形成一支“红学”,诸如此类足见这一时期新文化人对民间文化的“偏爱”,并非只是发生在俞、林、潘三位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带普遍性的趋向。
“五四”后新文化人于国学,由旧时的“注经”,转而为“释俗”,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重要学术转向。此一转向自有其时代趋会之因缘,盖因基于世俗生活的民间文化传统一脉更近于人性,因而与现代文化精神相通,故束缚人性的礼教儒学被抛弃后,作为其对立面的民间文化便成为既与现代性相亲和,又为民族文化一线所系之命脉,其被新文化人起用为建构新观念新文化的内在知识资源,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故“五四”文化人被后人冠以“反传统”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实是一种只以正统儒学为传统的误判,实则他们对以往居于下位的民间文化传统多有借助与延续。由此可见,在现代新文化、新观念建构中,除了西方文化这一外在的主要知识资源之外,民间文化传统应是另一支虽地位稍逊、但亦不容忽视的内在文化资源。对于此点以往人们多有忽视。至于这一脉民间传统的元素构成如何,其中何种元素与现代观念如何接续,以及对于中国现代观念建构有何影响等诸问题,更是值得作深入省察的课题。
他们三位除了上述共性之外,还因出身、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社会角色、价值观念及个性爱好的差异,对《浮生六记》的解读有以下两个不同点:
第一,他们三人因家庭观念的价值观和视域不同,造成对《浮生六记》符号意义的认知差异。
他们三位在解读《浮生六记》时都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新家庭观念,但其价值核心有所不同,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视域,在此不同视域下解读此书文本,便各自抽取不同的内容将其符号化,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故此这同一个文本在他们那里便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映像:在俞平伯那里是“个性伸展”的例证,在林语堂那里是“闲适生活”的样板,而在潘光旦那里则是“种族竞存”对立面“个人主义家庭观”的标本。由他们对《浮生六记》文本解读所形成的这种不同,可知他们建构现代观念中传统所承载的符号意义,是由其价值核心及其认知视域所决定的,经过这种“视域”的“过滤”,传统的原文本发生了意义的变异。于此可见,他们对于这一传统的解读和认知的差异,并非出于承载传统信息的文本本身,而是在于他们各自的视域不同。因而欲究传统在现代观念中如何延续,弄清认知者的视域——亦即“过滤网”的构造当是其关键。
第二,他们三人认识方法的不同,导致《浮生六记》符号意义的不同变异。
俞平伯推介《浮生六记》,意在宣传“个性解放”的“五四”启蒙精神,所以他见到此书便感叹是“一篇绝妙宣传文字”,他是以启蒙主义认识理路,有意识地将此书比附为“个性解放”的符号,加以阐发,加以宣扬。但是这种比附则混淆了沈复依附性的“个性伸展”,与现代人权意识基础上的个性解放观念之间的区别,从而使个性解放新观念的人权意识内核受到遮蔽。林语堂译介《浮生六记》,旨在向西方人展示中国文化的“优点”,他以西方中心的理路,将该书作为中国人“闲适生活”的样板而介绍给西方人,这种解读虽然很合正陷于工业主义忙碌生活之中的美国人的口味,但反销回中国,却出现了语境上的错位。而潘光旦引述《浮生六记》,则是以科学主义的理路,将其作为有害于“种族竞存”的个人主义家庭观的模式,但他的这种解读,也因其过于强调科学理性,而导致人文关怀意识淡薄,对个人利益与个人情感的忽视。他们三人分别所执的启蒙主义、西方视角和科学方法的认识取径,虽然对《浮生六记》的符号意义各自作出了有一定价值的开掘,但也产生了简单比附、语境的错位和工具理性的偏颇三方面的缺陷,代表了这三种认识取径对待传统的得失。这三种理路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文化认知方法,其对于传统延续的作用与得失,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究的问题。
今天距沈复泪写《浮生六记》已相去200年,距俞、林、潘三位解读此书也已逾数十载,而《浮生六记》在中国大陆又经过几十年的再度遗忘之后,近十数年来却又出现了再度的流行。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2003年,在全国各地出版社重印此书已达40余种版次[130],也可以说算得上“五四”以后的第二次热印。如果说“五四”那次流行的主流,主要是应和了俞平伯“个性解放”启蒙主义符号意义的话,那么,考虑到这一次林语堂的书也同时热印的因素,则此次林氏“闲适生活”的解读,似乎对于现今正陷于工业文明忙碌生活的中国人更合口味。显然,今天的中国人与当时林语堂所面对的中国人相比,所处之境况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当时语境的错位,在今天似乎变成了正位。于此可见,存在于后世观念中的传统,会因时过境迁而改变其意义,无论是文本,还是对其的解读,都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会有特定的意义。而在后世观念中所延续的传统,也只有在当时人的语境中,经当时人的解读才具有当时代的意义。传统也只有借助于这种语境的变换,才能够作为一种新意义符号而复活。过去了的传统,就是籍着后来的“变异”性的解读而延续其生命,其意义也会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异。故而可以说,在后世观念中的传统,只活在当下的解读之中,而其意义则取决于解读的主体、语境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