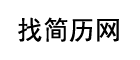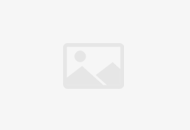文/杜都督
编辑/闫如意
就业越难,实习就越卷。
每年暑假,都是大学生实习的兵家必争之时。
今年是疫情开放后的第一个暑假,这条赛道上挤满了清澈稚嫩的大学生。
能越过龙门的总是少数,有的早早开始败兴而归,有的初出茅庐备受打击,还有的看似得偿所愿,背后还有更大的陷阱。
“没找到实习的暑假,我就像一支砸在自己手里的股票。”
虽然找实习这件事一年难过一年,但是今年又是客观原因对对碰中的“最难一年”。
开学就要大三的阿星,切身体会了这种痛。
今年年初,阿星放寒假时,北京正值疫情快速过峰期,学生不敢在北京多待,她的同学们都回家了。
阿星是北京人,只能驻守老家,阳过以后她顺手投了几个简历后,居然轻松地收获了几个offer。
而等到了今年暑假,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她从五月投到八月,某某直聘和邮箱一天进进出出八百次。
招聘软件上要么是“未读”,要么变成了灰色但是没有下一步,一直迟迟没有人联系她。
“想来是人太多了,疫情终于结束,大家都在疯狂补实习。
本来在北京上大学的人不走了,别的地方的大学生都来北京找机会;
还有原本在国外读书的学生,这也是他们第一个能回家的暑假,有些人也想回来找找实习。”
1年前,甚至有一家头部公关公司主动联系她来实习,当时她因为太忙、太累、不想去,放弃了那次机会。
这次她再投,别说进面试,就连自己的简历也已经递不进别人的备选人才库里。
阿星的研究生准备申国外的学校,她需要实习经历,在今年暑假之前,她做过三段实习,而这只是同学们的平均数。
“之前的都不算高质量,所以这次都投的是头部公关公司,后面,发现怎么还没联系我呀?
人一焦虑,标准就会下降,降到最后自己投的也是不想去的地方,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对于广告专业的“走走”同学来说,这个夏天也是她的一道坎。
有一句话叫“大三还没有一份实习就废了”,这在即将升大三的走走眼中,无异于一条“死线”。
她之前从来没有实习过,但今年恰好撞上了最难的一年。
她原本还算有信心,她的专业是全国第一,而且她也不打算海投——
曾经她在学校参与过一个潮玩品牌合作的比赛,这次还打算投她们。
对方的面试分为几轮,筛选简历、参与笔试并完成两份策划、通过之后才能拿到面试邀请的入场券。
面试那天“走走”特意和老师请了假,和对方聊了半个小时,结果大跌眼镜:
“我觉得我们谈的还挺愉快的,但我最终也没拿到offer,因为他们认为我没有实习经历。”
第一份最有希望的实习突然猝不及防消失了,假期还没有着落,她赶紧给手机上下了3、4个app,按着“一键投递”的按钮,开始疯狂投简历。
中间也有一两家公司看到了简历,愿意从人群中把她扒拉出来要请她参加笔试,但是能进入面试的一个都没有了。
受挫的“走走”向师哥讨教,对方告诉他,自己从大二上就开始实习了,但是今年暑期也尤其困难,对方是投了30份,才能最终确定这个暑假能去哪里。
走走突然感觉,自己哪怕才大二,在社会时钟里,她已经迟到了——
在她们系,有的人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开始实习的;
还有同学更是自从来北京以后假期就没有回过家,每个假期都在北京各大公司当实习生;
上课时间撞上的话,他们会翘课去,偶被老师抓到就会找借口圆过去……
“大三找不到实习就完了”的威胁言犹在耳,走走像填高考志愿的18岁一样焦虑,然而这次,生活已经不能给她标准答案了。
她最开始还会用ps做简历,针对每一家简历进行针对性修改,排版,投递邮箱。
然而一次次地失败、拒绝、“简历未被查看”的话,都让前面的努力变成了精心制作的废料,走走开始痛苦,甚至自我内耗。
到最后,不停地修改自我认识使她的标准已经无限下降了:
“我的标准已经下降了,从能有一个实习变成能有公司让我参加他们的面试了。”
比起被crush吊着,更痛苦的是被工作漠视。而这往往是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课。
“不合适的28份,待处理的13份,被查看的4份……每天都这样,但是我习惯了。”
学计算机的陆浔自从找实习开始,就在收藏夹里嵌好了每一个招聘的网站。
最开始这些是想要攻占的kpi,后来投来投去,就大多变成了落败的标的物。
直接被拒还算干脆,习惯打电话邀约面试的大厂才会令人神情紧绷:
“因为他打的电话是单向的,接不到就打不回去,为了等这个电话,我需要一天都开着手机。”
他投简历的大厂,哪怕是暑期实习、不保证有留人机会,也大多数都要足足经过一轮笔试和三轮面试,一共四轮,每一轮都需要好好准备。
然而同时投递,大家反馈的时间又十分接近,A厂一面叠着B厂的二面,通过考核的快乐只是一瞬间,来不及好好准备很快就需要投入到下一场强度更高的专注力测试中。
最恍惚的时候,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最想去的公司给了他一个笔试机会。
他以为笔试时间2小时,在这天答完就行,但其实人家有规定的集中时间,等他点开网站链接时候,只剩一个小时了。
“答的稀烂。”
时间像一个被卷在两场面试中的车轮,受挫和压力令他整个人又疲惫又焦虑:
“我既害怕电话来得太快,没准备好就面试,又害怕他电话永远都不来。”
所有的岗位,和陆浔竞争的报名的都有三四十个人,清北、C9、国外的名校在这里能做连连看。
所有人都在虎视眈眈,等待一个能从天而降的机会。
毕竟这届年轻人已经被分成了两个流向,在“最好的工作”这个命题里,一边人流向了体制内的铁,另一些人选择了大厂的卷。
只是在默默之中,大厂已经不再是当年最风光时候的模样,但仍然有人往这里涌来。
身边的人和他一起抗压。
往年投了就能就去的岗位,陆浔说今年连简历初筛都过不了;
有人实在找不到大厂的实习机会,就索性去了外包公司,这是他们大一大二就能找到的工作,现在五年过去了,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知识,研究生即将毕业,却又回到了原地。
某大厂广告部门的一位知情人士说,这两年实习生的名额已经被砍掉不少,他所在的组从去年暑假就没有实习生了。
“流量红利没有了,早些年扩招招人太多,现在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缩紧队伍。”
然而,整体的痛苦是虚幻的,身为个人的受挫却是切实的。
准实习生们只会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强大,毕竟就算名额再少,总有人能成为“挤破头”的那一个。
如果实在太难,有些人已经开始在迫不得已下,寻找新的“门路”。
在一所普通一本大学读金融本科的小鹿,暑假根本找不到实习的去处。
他原本觉得自己只是“没那么拔尖”,但是放在整个金融实习市场上,简直完全“不够看”。
“我想去的地方只要985和两财一贸,要有投行经验,要能加班,要考过CPA。”
然而这样的地方,给予的却极其“吝啬”——
有的地方招来的只是“小黑工”:不签合同,不给钱,让你干活;有的地方没有实习证明;而有些是众所周知的“只要男生”。
然而因为含金量高,要求再苛刻,也能每年招到心甘情愿的实习生。
“我自己是海投,那top10和海外qs前50也肯定海投啊,像我一样的人可太多了。”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鹿的简历,一出手就石沉大海。焦虑、内耗、自我否定,压力像空气一样将他裹的密不透风。
最后,小鹿决定另辟蹊径:“直接花钱找付费实习吧,反正投来投去都会碰壁,我不想再接受打击了。”
不过令他没想到的是,哪怕同一个职位,在市场上也有不同的价格,有的付费中介卖几千,有的卖几万。
“那种保证下全职offer的要几十万,我都吓得没敢多问。”
在金融圈,付费实习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
小鹿听说自己有个学长,靠机构推荐有了第一份实习,靠这份敲门砖越走越好,最后去了三中一华。
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和最后一根稻草的执念,咬咬牙花了2万3,在学长走的那家机构挂上了名。
然而这个动辄上万的“名利场”,中间也有很多的弯弯绕绕。
博主“大力如山”曾经科普过,付费的金融实习,要么是空手套白狼,他们手里根本没有内推机会,要么只是“小黑工”。
我提醒小鹿小心受骗,对方也很无语:
“我知道这些付费的没那么靠谱,他们的保证就像偏方保证生男孩一样,但万一呢?毕竟我也没别的办法。”
有人说过,实习生的至爽时刻,是收到offer的一刹那;
而至暗时刻,是除了那一刻的所有时刻。
小鹿比较幸运,他信任的“工作室”没有立刻拿钱跑路。
他甚至在一个月后就拿到了一份颈部券商的工作实习机会,有offer有协议,而且“支持背调”。
小鹿开始变得很忙,工作内容也不完全是他喜欢的,但是思考了一下后,他很快释怀了:“有一份活干就行了,这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吗?”
不过最近,听到越来越多人付费实习被查出来了,直接在入职时候就被pass掉了,他有一些紧张:
“这份结束了我再自己找找实习吧,最好把简历洗一洗,好看一点,到时候争取这份花钱的不用出现在我的简历上。”
很难说对于一个没有经济独立的人来说,花2万3获得一份未必能写在简历上的实习会不会后悔。
但是对他来说,它已经是自己焦虑时候最珍贵的药了。
人一旦降低标准和期待,一切好像变得很容易解决。
比如走走,她最初的理想是获得一份4A、公关、甲方、或者互联网大厂的实习。
但是当被现实无限打击过后,她在学校大群里看到一份视频剪辑的工作,觉得也不错,她像往常一样投了简历,后来这成了她第一份实习。
“我找到这份已经投了20次了,虽然和我期待的不一样,但是这是我第一份实习。
大家都说第一份实习很难找,万事开头难,后面就会好的。”
即使已经有了着落,她一直还在复盘,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利用疫情在北京的时期多找找机会,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捉襟见肘。
“就怕一步错,步步错。”
我问走走,她觉得自己现在算不算“上岸”,走走苦笑一声说,现在还不算,直到确定了下一个实习吧。
我追问如果这一段结束,能去到一个4A公司,那样的话算不算上岸,走走想了一会:
“那也只算阶段性地上岸,因为我发现了和别人的差距,要走的路太长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做。”
陆浔折腾到最后,退了几层皮,总算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厂实习。
但是从另一面说,他的代价也很大——他正在跟着导师在做项目,实验室要打卡,项目进度一般,但是他还需要每天出学校上班。
时间冲突,只能二选一,他和老师争取了一番,中间差点遭遇“退学警告”。
最后斗争的结果是,他退出了项目组。那么在最后一个学年,他除了找工作以外,还要完成自己的毕业设计。
他说现在自己的生活是在“最厉害的互联网大厂里整理文档”,他拥有了留下来的可能。
但是当他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组长带头熬夜加班到一两点,又令他掐断了想去大厂就业的心:
“干不完,活多的根本干不完。我现在觉得生活还行是因为我是实习生,但是正式入职这样连实习期都过不了,我怕被毕业。”
他的理想工作从大厂变成了国企。下半年快秋招了,他要一边实习、一边毕业、一边找工作。
“我只有在找到实习,和辞职的那两刻是快乐的,其他时候都是迷茫的。”
时间和人生好像变得很简单,被一条条名为“目标”的线分割,摸不到这条线,就永远在冰冷的水里。
所谓的“上岸”,也离陆浔很远,大概要游好一阵才能到。
“可是什么又算岸呢?”